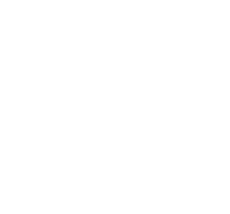3个最本土的中国乡村建筑
来源:乐鱼体育官网下载 发布时间:2024-09-17 06:32:39
2月27日,“乡筑未来奖”在展会“设计深圳”的主论坛上颁布。这是中国首个“可持续乡村建筑实践奖”,从9组入围作品中选出3个,分别表彰它们在建造、活力与模式上的可持续。
奖项发起者之一、建筑师王俊锋说,是时候跳出设计类别,来看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慢慢的变多的中国年轻设计师“上山下乡”,乡村已然是我们中国式建筑实践的新的实验场。
华人青年建筑师社群“践谈APT”和设计深圳共同发起“乡筑未来奖”,分为乡筑建造奖、乡筑活化奖、乡筑共生奖三个类别。图为“乡筑未来奖”获奖作品
一条家居设计借此连线位最终获奖的设计师和奖项发起者之一王俊锋,并梳理了3个获奖作品:一间位于大理沙溪镇的酒店,化用当地白族村落的结构,建成夯土房;
一个背靠田野的驿站,脱胎自原本要废弃的村屋,用3个月为附近乡邻造一处茶余饭后看风景的地方;
一个位于四川的整村设计系列,不仅关注当地人的住与行,也考虑怎么吸引年轻人回乡。
2017年,我还在美国工作,一次旅行中结识了“喜林苑”的创始人林登先生,受他的邀请来到云南大理沙溪镇的石龙村,为“喜林苑”的新酒店做设计,新项目占地1万多平米。
我在美国时,设计工作主要以城市CBD、超高层建筑为主,所以对于中国的乡村非常期待。导师曾经对我说:如果你要回中国,就要用脚去丈量每一寸土地,这样才可以更了解你的国家。我觉得,这是支撑我回国做乡建的初衷。
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选址在沙溪石宝山森林公园的最深处,一片山谷坡地之上,傍湖而建。山脚下是热闹的沙溪古镇,山腰有被喻为“南敦煌”的石钟山石窟,大山里居住着的,是最原生态的白族村落。
从2017年到2020年的3年时间里,我几乎都生活在云南,亲身体验那里的气候、环境、民俗。
沙溪的乡村环境相较于江浙地区更为“原始”,村民们依旧在从事着农业生产,以田野和山林为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所以村子的聚落感非常强。
整个酒店1万多平米,由于只选择了被畜牧和种植破坏过的山地作为建设用地,所以仅有10间客房,全部做成独立别墅院落的形式。10栋房子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小型的“村落”,“村落”中还有公共空间,就像村民们集会、唱歌、跳舞的小广场。
住宿区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夯土,这是90%的白族民居都会使用的乡土材料。虽然被民间普遍的使用,但它依然是一种“非标准”材料,在防水、力学性能等方面没有统一规范,常常有裂缝、掉土的情况。
所以首先,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村民们一起去研究土。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没有谁去引导谁,而是互相学习。比如我会带着做夯土的师傅去参加法国专家的材料研究工作营,村民们也用自己的经验去辅助我们的实验,最终采用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就是师傅在无意中摸索出来的。
夯土有不同的颜色和性能,在尝试了很多次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如果以特定的比例将红土和黄土进行混合,就可以同时解决开裂和掉粉的问题。这个小小的发现让师傅们至今津津乐道,有位师傅还把这项技术用在他自己家新造的房子里。
我们尝试的夯土建造、聚落格局、公共空间,从材料到原型都来自白族民居,所以,新建筑不会成为当地的“异物”,也不会“入侵”村民的生活。
共同建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房子,让村民们真正地对这个建筑产生了情感认同。我有一次从丽江的机场去酒店,恰好搭了一个村民的车,他一路上都很自豪地向我介绍喜林苑·沙溪的项目,那一刻确实让我挺欣慰的。
因为石龙村交通不便,很难与外界互通,比较闭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希望带动村民参与服务业、稍稍提升生活品质,就需要调动起他们的认同感。
在5年前,大理的部分建筑,无论是带有传统民族装饰纹样的新建筑,还是偏地中海风格的度假民宿,可能对旅行者来说,都少了些与本地的连接,这是我们项目思考的起点。那么设计能否成为桥梁或媒介呢?建筑如何可持续的“生长”在乡村之中?这也将是今后我们大家都希望持续去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一直说我们是真正的“草根团队”,没有名校、海归的背景,也没有多“酷炫”的设计,有的就是对村子的陪伴式服务。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吃住都在村子里,不在村子,也在去往村子的路上。
位于福建南平市龙斗村的“瑶理田园驿站”,其实算我们团队第一个落成的项目,建造前后只花了3个月,从项目开始到获奖,都充满戏剧性。
拿到这一个项目非常偶然。我们原本在做隔壁村的改造,路过龙斗村的时候就来看了看。当时村委会很稀松平常地指着一栋一层平房说:这个能拆掉。但在我们看来,建筑原本的结构完好,又有着可以看稻田的良好视野,存在很大的改造空间,不必拆掉。
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几乎“没有甲方”的改造实验,唯一的要求就是——快。
我们决定把这栋原本要被弃置的平房,改造成村民和外来人都能使用的休息驿站。整一个完整的过程里,一边设计,一边施工。有时候负责施工的老乡看不懂专业的施工图纸,我就手绘给他;有时候可能离开了半天以后再回来,发现有些细节做得和想象中不一样,那我们就接受“不完美”,这才是真实的乡村。
一层平房是砖混结构,之前作为仓库使用,堆砌杂物。我们改造时,完全采用“套建”的方式:把加盖的2层直接“套”在一层上,原始的建筑结构全部保留,只更新门窗。
加盖的部分,是轻盈的小型钢结构与板材墙面,屋面用的闽北乡村最常见的雨棚屋顶,它轻薄、扁平,成本也很低廉,当地村民做建筑改造、扩建时,也会选择这种材料。
在2层,我们做了洄游式的观景走廊。第一眼看到这一个房子时,我们觉得它其实很浪漫:一侧能看到田野,另一侧能看车流。
能看到车流的一侧,做得更亲切一些,加了一排悬挂式的“美人靠”,村民们不光可以朝里坐,也可以倒过来、把腿伸到屋檐之外,更放松地发呆。
“美人靠”造好之后,我一度担心,大家能发现这条长椅的坐法吗?我需不需要在旁边加一些引导性的标识?没想到,房子一完工就迅速在十里八村传开了,等我再回去看的时候,那条悬挂式的长椅上已经挤满了人,大家很自然地找到了最舒服的坐姿。那一刻我明白了,建筑本身,就可以引导人们调适行为。
如今,田园驿站真成了附近村民们茶余饭后都会来的地方,他们对建筑也有了全新的认知: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可以因为一栋房子而被关注、汇聚人气。接下来,当地村委会也考虑,在村子里增加民宿的功能,村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创收方式。
我们团队在2020年成立,疫情期间,项目来源和收入都不稳定。那时加上我只有4个女生,在别人眼中,我们总是很开心地上山下村,马不停蹄的奔走在各个村子间;但其实多数时候我们白天背着工具去测绘、调研,晚上回到没有空调的小房子里,冷飕飕的,围坐在一起讨论设计。
我们确实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大众茶馆设计项目,收入上,肯定还是不比在设计院里拿着每月的工资要稳定。但对我们来说,坚持做这件事情是很快乐的,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十年之后才投入到乡建中,乡村的活力和自然可以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17年,因为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与小石村的村支书岳付飞相识,得知了他们盼望借助设计师的力量去改变村子的现状。
小石村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重要的受灾区。以前,村民们就沿着道路和水系去盖房子,农户的家和耕地都散落在山里;但震后为了快速重建,就把这些散落的农户全都部集中在一个小区里,耕地和住宅的距离很远,村民们的居住和生产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仅如此,在震后村子的规划中也欠缺对于公共空间的表达,我去看场地的时候,发现村民之间没有聚会,没有沟通,在密集的小区房里,大家就是窝在家里看电视,出来聊天也就是蹲在墙根底下。
2017年,正是民宿兴起的时候,岳书记最初的想法,也是希望我设计一个民宿,为村子带来一些收入。但经过对小石村的观察和调研,当时那个情况做民宿可能困难重重,首先还是要先解决乡村本身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终选择先造一座公共建筑“文化大院”,用一个“大屋顶”,囊括村民们的一切公共活动,重构身份认同。
文化大院的选址在小石村的中心,包含了日间照料中心、乡村卫生站、乡村夜校、健身房、忠孝文化展厅等。设计上,用四坡瓦屋顶来统领全局。我们在屋顶的四坡分别打开四处天井,茂密的竹子从天井中“冒”出去。屋檐下的空地,就成了村民闲聊、遛鸟、观看露天电影的文化场所。
另外规划出“社区粮仓”:农具清洗、存放,农作物晾晒、储存,红白喜事——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我们留出阳光最好的一块地,让村民们晾晒农作物,或举办当地的“坝坝宴”。
有了可以聚拢村民的文化大院后,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每户村民的住宅改造,希望以最小的干预去解决公共空间缺失的问题。
现在的小石村,非流动人口不到1000人。大家住的房子要么就是跟城里一样的单元楼,要么就是一大家子一栋的2层小楼。村里主干道两侧的100多米内,分布着20多户人家,我们就做了一件小事:加屋檐。屋檐2-3米不等,故意做得比传统的大。
有了能遮风挡雨的屋檐,村民们特别高兴,纷纷从屋里走了出来,沿街摆上麻将桌、饭桌。孩子能在屋檐下写作业,老人可以做竹编活儿,村子也就“活”了起来。
我们在小石村5年,改造的第一阶段,基本针对公共建筑、沿街空间,先把最基础的社区公共空间建立起来;第二阶段就是引入一些具有盈利性质的项目,包括共享民宿、工厂,以及后来改成酒店的这一些房屋,都是希望能将更多就业岗位带出来,让村子在未来可以自主的“造血”,创造价值。
我想第三个阶段,就是触及到周边的城市,去建立引入外部资源的一个良性循环。前两个阶段已经实行得很有成果,第三个阶段因为疫情的原因而中断了,但今年,许多项目或许又能重新启动,小石村又会有一些新鲜的变化吧。
我是北方人,小时候家里的房前屋后有很大的院子,种上二三十种农作物、十几种果树,邻里之间的交流也特别丰富。上小学之后,开始住楼房,就觉得跟自然的连接渐渐消失了。
在小石村的日子,让我重新找回熟人社会的亲切感。前几年,我们基本每个月都会去村里,每次去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和村民们聊聊天,他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烨哥”。
改造之前,对村子的第一印象是有些普通,现在再去,就觉得变化很大:村子里越来越热闹,村民们的生活景象非常鲜活。在乡村,人们只有多见面,人情与文化才会慢慢萌芽、生长。
Q:此次“乡筑未来奖”是由华人青年建筑师社群“践谈APT”与设计深圳共同发起的,作为“践谈APT”创始人,可以谈谈初衷吗?
A:设计深圳(设计上海团队)其实是比较关注城市的一个展会,但随着乡村问题被慢慢的变多的讨论和研究,其实关注的视角可以是更为宏观的——不局限在某个设计的类别,不局限在城市与乡村,而是关注“什么是中国式设计”。
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上山下乡”的这样一个奇观,让乡村建筑实践变成了我们中国建筑实践的一个试验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我们践谈APT社群里的很多年轻建筑师也是这种奇观的一部分。
所以2022年3月,我们和设计深圳就开始去策划这个奖。最初,我们并不想做奖项,不希望它成为一种奖项经济,而是希望可以通过一年一度的评选去逐渐建立一种评价体系,对慢慢的变多的乡村建筑实践提供正向的价值引导。我们常常说城市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那么对于乡村来说,什么是真正有效、能够融入到整个乡村体系中的建筑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长期探索的话题。
评选不是目的,最终,我们期待这套评价体系能够日趋成熟,奖项本身就是一个集结号,它所筛选出来的优秀设计力量也能够集结成一个“智囊团”,链接到有需求的乡村中,这会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价值。
首先是Condition_Lab & UAL Studio的高步书屋,他们一直在探索侗族的建造体系、生活方式,从中能看到很多人文的东西,看到乡村生活的组织架构,这些都是建筑师真正融入乡村后,经过陪伴式的成长才能够逐渐提炼的。
他们有一张照片,书屋的灯光点亮了,很温暖地“躺”在它所处的乡村里,就像灯塔一样点亮乡村,那个瞬间特别打动我。建筑师不是以一种外来闯入者的姿态、带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去设计,而是试图在理解当地的前提下再去做突破,既是破局也是入局,是两套价值体系之间的抗争与融合。
还有就是李烨老师的小石村改造,也是一张照片——年轻人在村子里跑步。看到这张照片就可以感觉到他们通过乡村的建筑实践,搭建出一个底层逻辑、一个框架性的方法论,然后利用这套方法深度地参与到整个乡村的运营当中,最后把年轻人也吸引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成果。
Q:谈谈您本身作为建筑师,在进行乡村(或城市更新)实践时,是如何去调动当地的资源、活化空间的?有哪些亲身的心得体会?
去年我们得当设计在苏州吴江的八坼街道老街完成了一个微更新设计,那里离运河仅仅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也是一个高密度的小乡镇环境,和乡村中类似的熟人社会。
在踏勘之后我们就感受到了小镇的活力的缺失和相对的空心化,所以我们和李烨老师他们在小石村的设计策略实际上有点相似,是通过营造一个公共空间先把大家凝聚起来。
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中,镇里面的“老娘舅”起到了很大的调和作用,因为他非常知道每家每户在想什么,由他来收集意见、传递和解释信息更能够让大家安心。我觉得更新、改造永远不能硬来,调动资源、活化乡村都需要极大的耐心,是每个乡建者必不可少的工作。